趙其國:奔走大地尋沃土
時間:2020-01-21 21:45:12 來源: 已閱讀:0次
1996年夏,在中國科學(xué)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資料室查閱資料���。

1966年在古巴野外考察,趙其國(右1)給大家講土壤標(biāo)本的采集方法。

1977年11月,在黑龍江進行荒地考察時與同事一起研究工作���,左2為趙其國���。
趙其國 中科院院士���,土壤地理學(xué)家。1930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漢市���。1953年畢業(yè)于華中農(nóng)學(xué)院農(nóng)學(xué)系���。1983年晉升為研究員,1991年當(dāng)選為中國科學(xué)院院士���。歷任中國科學(xué)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長���,中國土壤學(xué)會理事長,國際土壤學(xué)會常務(wù)理事���、鹽漬土分委員會主席等職���。從事我國及世界土壤地理與資源的研究���,特別是對熱帶土壤發(fā)生分類、資源評價等進行了系統(tǒng)���、深入的研究���。
從零開始識土壤
1953年7月,趙其國從華中農(nóng)學(xué)院畢業(yè)分配到中國科學(xué)院南京土壤所���,不久���,即由組織決定,跟隨華南工作隊到華南一帶進行土壤調(diào)查工作���。
這次土壤調(diào)查對趙其國來說是第一次���,很多東西是以前在學(xué)習(xí)中沒有接觸過的,因此必須在工作中踏實地從頭開始學(xué)起���。
其時���,對趙其國影響最深的���,當(dāng)屬此次華南橡膠宜林地考察的領(lǐng)隊李慶逵。
李慶逵本人是學(xué)農(nóng)業(yè)化學(xué)的���,白天馬不停蹄地去考察,晚上還要給年輕人上課���,講肥料���、講化學(xué)。為了讓新來的人盡快了解土壤學(xué)方面的知識���,掌握土壤調(diào)查和肥料試驗的技術(shù)���,李慶逵可謂費盡心思——在布置肥料試驗時,他向年輕人詳細講解施肥的基本原理���、方法���、理論根據(jù)���;計算肥料時,又詳細講解關(guān)于土壤化學(xué)方面的知識���;另外���,只要有人向他請教牽涉工作與業(yè)務(wù)上的知識時,他總是毫無保留地耐心講解���。
趙其國喜歡聽李慶逵的講解���,記了大量的筆記,每次考察一圈回來都會有一兩本的筆記���。有些內(nèi)容李慶逵也不指定書目���,趙其國回來自己在圖書館找書慢慢再補。
趙其國充分認識到���,要搞好土壤科研工作���,對他這樣非土壤學(xué)科班出身的人來說���,通過工作學(xué)習(xí)是很重要的。因此���,在工作中他特別注意從最基本的學(xué)起���,積極爭取做具體煩瑣的工作,如打土鉆���、采標(biāo)本、寫標(biāo)簽等���;同時���,在工作中遇到問題多提問,哪怕是最基本問題���,只要沒有聽懂或者沒有深入理解就及時請李慶逵再講解���。這樣,他在業(yè)務(wù)上提升很快���,不久就可以獨當(dāng)一面開展工作了���。
艱苦的橡膠宜林地調(diào)查
新中國成立后���,國家經(jīng)濟建設(shè)處于恢復(fù)期,百業(yè)待舉���,民用工業(yè)���、國防工業(yè)急需大量天然橡膠,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全面禁運���,天然橡膠作為戰(zhàn)略物資���,是禁運的重點。1950年10月���,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���,我國天然橡膠供應(yīng)更趨緊張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���,中央果斷作出“一定要建立我國自己的橡膠生產(chǎn)基地”的戰(zhàn)略決策���。
剛出校門的趙其國就參加了全國具有戰(zhàn)略意義的橡膠宜林地調(diào)查���。在李慶逵等人的帶領(lǐng)與指導(dǎo)下,與一大批熱血青年深入到雷州半島���、海南島���、西雙版納等深山密林中開展工作。
考察的時候常常要鉆無邊的森林���,林子里有大象、蟒蛇等各種各樣的動物���,曾經(jīng)有一次���,趙其國踩在蟒蛇身上都還不知道。因為在野外比較危險���,所以都是軍隊派人帶著武器���,跟隨考察隊員一起進去���,一個小組一般20多個人,其中解放軍10名���,考察隊員10名���,一對一地保護。有時遠遠一看���,就像押著犯人一樣���,早上一個個押進林子里去,晚上再一個個押回來���。有時林子比較大���,走得比較遠,晚上考察結(jié)束了出不來���,就全部在林子里宿營���,有好幾次鉆在森林里五六天才出來���。
鉆林子十分辛苦,別的不說���,單單螞蟥就讓許多人受不了���。那時穿的襪子是防螞蟥的,是用比較厚的布做的襪子���,襪筒比較長���,可以套在褲腿外面,然后拿布帶子再綁扎起來���。但螞蟥太多了,在前面第一個走的人要好一點���,最后走的人���,身上能爬幾十條螞蟥���。有時候被螞蟥吃得沒辦法,有人專門用香煙紅紅的煙頭���,在螞蟥吸過的傷口上燙一燙���,燙腫了血就止了。幾乎每天都過的是這種生活���,也沒有人叫苦���。
1958年,趙其國擔(dān)任考察隊的領(lǐng)導(dǎo)���,在西雙版納等地開展定位觀測研究���,通過長達10年之久的野外調(diào)查、研究���,總結(jié)了以橡膠為主的熱帶作物開發(fā)利用與土壤分布及土壤性質(zhì)的相互關(guān)系���,提出了以熱量條件���、土壤性質(zhì)為標(biāo)準(zhǔn)的熱帶作物利用等級評價方案,為制定熱帶作物發(fā)展規(guī)劃與布局提供了科學(xué)依據(jù)���。
受命援建古巴
1963年���,毛主席接見卡斯特羅后,決定從中國派土壤���、漁業(yè)���、文化等專家組赴古巴執(zhí)行國際援助項目。次年9月���,中國科學(xué)院南京土壤所組成地理���、農(nóng)化、物理���、溫室等專業(yè)的援古土壤專家組,由李慶逵帶隊到古巴正式開展工作。專家組的主要任務(wù)是在3至4年內(nèi)援助古巴科學(xué)院建立古巴土壤研究所���,并結(jié)合開展古巴土壤考察研究���,培養(yǎng)古巴土壤研究人才。整個工作從1964年底正式開始���,一直到1969年1月才結(jié)束���,前后歷時4年。
幾年來���,趙其國帶領(lǐng)七八位古巴年輕土壤工作人員���,分乘幾輛吉普車,跑遍古巴5省1島���。每天清早出發(fā)考察���,采土、制圖���、訪問���,中午吃點面包和水���,下午繼續(xù)工作,到4點返回駐地整理土壤和植物標(biāo)本���,晚上還要討論第二天的工作計劃���。每天的工作地點不一樣,工作內(nèi)容基本相同���。就這樣周而復(fù)始���,幾年中人員不變,吉普車卻換了4輛���。通過幾年的工作和生活���,古巴方面對中國專家多年長期在外工作的刻苦耐勞、團結(jié)友好���、堅持不懈的國際主義奉獻精神十分敬佩���。
過去美國人曾在古巴進行過土壤研究,但有組織���、有系統(tǒng)地全面開展土壤研究���,是從中國專家去后才開始的。趙其國在古巴先后擔(dān)任專家組副組長���、組長���。他除領(lǐng)導(dǎo)創(chuàng)建古巴土壤所、培養(yǎng)干部外���,還負責(zé)進行古巴土壤性質(zhì)���、土壤地理及資源利用的深入研究。首次對古巴土壤地理工作進行系統(tǒng)總結(jié)���,對該國土壤資源評價���、土壤發(fā)生分類等提出新的概念���,最后完成了1∶25萬古巴土壤圖及《古巴土壤》專著,由古巴科學(xué)院正式出版���。這兩項成果不僅對古巴的土壤研究具有重要指導(dǎo)意義���,而且在國際土壤學(xué)界產(chǎn)生了影響。
8年的黑龍江“候鳥”生涯
上世紀70年代初���,周恩來總理曾親自部署向“北大荒”要糧的任務(wù)���。當(dāng)時組織了全國有關(guān)科技力量,在黑龍江省進行荒地資源考察���,建立商品糧基地���,力爭向國家提供25億公斤糧食。黑龍江省荒地資源考察任務(wù)是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在“文革”后接受的第一項國家任務(wù)���,當(dāng)時任所黨委書記的沈現(xiàn)倫極為重視���,緊急抽調(diào)下放泗陽的趙其國回所���,由他帶隊并組織有關(guān)人員成立了土地資源考察隊。
黑龍江省過去統(tǒng)稱“黑土地”“北大荒”���。趙其國帶著所里的20多個人,和中科院其他6個所來的人���,一共300多人���,再加上黑龍江省抽調(diào)的農(nóng)業(yè)廳、國土廳���、財政廳的人員���,總共有1200多人。這些人分成4個小分隊���,趙其國擔(dān)任西部分隊的隊長���。
在黑龍江的野外調(diào)查前后持續(xù)8年才完成���。每年,趙其國他們在5月1日當(dāng)?shù)赝寥阑瘍鰰r過去���,直到11月中旬土地上凍了���,他們才能坐火車回南京。每年在黑龍江要連續(xù)工作7個月���,他們像候鳥一樣夏去冬回���,一直連續(xù)了8年。
野外調(diào)查非常艱苦���。由于“北大荒”平原夏季地面淺層積水���,只能坐用紅松大板架成帳篷,前面用拖拉機拖行的“爬犁”���,并在其上生活���、采土樣���、查地勢、劃圖表���、選耕地���。住的是“爬犁”上的帳篷,吃的是饅頭���、大米、野菜���、天然蘑菇���、狍子肉、“飛龍”���、“四不象”等���,喝的是溝水,白天工作時常有蚊蟲叮咬。
北大荒野外蚊子很多���,一種個頭比較大的���,當(dāng)?shù)厝私?ldquo;牛蚊子”,還有一種是個頭很小的蚊子���,叫作“虻”���。“虻”能鉆到衣服里面,戴紗帽都不行���,鉆進去就咬���,經(jīng)常咬得趙其國他們身上到處是紅點。有時候脖子上咬得一大串一大串的���,又疼又癢���。等到休整的時候,才可以到縣里的醫(yī)院找一些消炎藥回來抹���。
幾年來���,趙其國與科學(xué)院和省里許多人共同投入了這場戰(zhàn)斗���,最終選出了4000萬畝宜農(nóng)荒地,并指導(dǎo)當(dāng)?shù)亻_墾種植���。在軍民共同努力下���,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,開墾荒地250萬畝���,增產(chǎn)糧食10億公斤���。
攻關(guān)黃淮海低產(chǎn)田
新中國成立以來���,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黃淮海平原的區(qū)域綜合治理工作���,先后對海河、黃河���、淮河進行了大規(guī)模的整治���。上世紀60年代將其列為全國十大農(nóng)業(yè)綜合試驗區(qū)���,“六五”和“七五”期間,又將中低產(chǎn)地區(qū)綜合治理納入國家科技攻關(guān)計劃���。
在國家號召開發(fā)黃淮海平原時���,趙其國親自領(lǐng)導(dǎo)了國家攻關(guān)項目“黃淮海平原豫北地區(qū)中低產(chǎn)田綜合治理開發(fā)研究”,依據(jù)熊毅等老一輩科學(xué)家積累的治土改土經(jīng)驗���,通過對8縣近13萬畝鹽堿���、風(fēng)沙、洼地的治理開發(fā)���,使這一地區(qū)的糧食產(chǎn)量和人均收入3年翻了一番���。
為了做好工作,趙其國每年有7個月在封丘辦公���,似乎他這個土壤所所長的辦公室不在南京而在封丘���。結(jié)果土壤所的很多工作也都圍繞著封丘展開���。當(dāng)時在封丘集中了兩三百人,有土壤所的���,也有其他單位的���,大家都在為土壤所主持的工作而連軸轉(zhuǎn),中科院十幾個所的副所長也都在���。趙其國擔(dān)任大隊長���,他以身作則做榜樣,一頭扎在封丘不走���,這樣其他人也都安下心來���,為國家實現(xiàn)糧食增產(chǎn)拼著命干���。
當(dāng)時的條件很艱苦���,大家住在萬畝試區(qū)���,房子根本不夠住,就在試區(qū)里搭棚子住���。一到晚上���,有人睡在桌子上,有人睡在地上���,趙其國也打地鋪���。沒有汽車,就兩個人騎一輛自行車���,到田里去不能騎自行車���,就靠兩條腿走路。每天早上出去的時候把饅頭背在身上���,因為中午常常沒有時間回來吃飯���。即使回到駐地���,食堂也是開大灶。當(dāng)時群眾生活水平很低���,他們跟村民同吃同住���。當(dāng)時主要靠“三紅”度日,即紅薯���、紅高粱���、紅辣椒,吃得飽���,但吃不好���。
科學(xué)試驗要有數(shù)據(jù)的測定。而當(dāng)時的數(shù)據(jù)都是用很原始的手工操作辦法測量出來的���,是每個人一點一滴親自干出來的���。他們每天都要拿著溫度計在地里測,包括水���、肥���、氣、鹽的變化都要測定清楚���。每一個田塊都有數(shù)據(jù)���,每一個田塊的產(chǎn)量,都能說清楚���。糧食收獲量都是自己去麥場打糧食���,肥沃田地的收獲、貧瘦田地的收獲���,都要進行測量和對比���。既要做到科學(xué)性���、真實性,又要能夠達到可推廣性���。
那時���,很多工作國家根本沒有多余的力量來組織驗收,趙其國便要求大家:“我們自己做的工作我們自己對國家負責(zé)���,我們自己都不確定的結(jié)果千萬不要吹���。”
1993年,黃淮海平原綜合治理與開發(fā)項目榮獲了國家特等獎���,整個工作告一段落���,趙其國才搬回南京土壤所辦公。
黃淮海農(nóng)業(yè)綜合開發(fā)治理的戰(zhàn)役���,推動了整個華北平原農(nóng)業(yè)的發(fā)展���,整個黃淮海地區(qū)的鹽堿土改良���,促進了糧棉油���、畜牧業(yè)的發(fā)展���,為該區(qū)域的糧食增產(chǎn)、農(nóng)業(yè)開發(fā)作出了貢獻���。
悉心開展紅壤研究
中國南方的一大片國土都覆蓋著厚厚的紅壤���,趙其國有幸在年輕時就跟隨李慶逵一直研究紅壤。經(jīng)過長期潛心研究���,在熱帶土壤發(fā)生及紅壤物質(zhì)循環(huán)與調(diào)控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績���,首次明確提出我國紅壤具有古風(fēng)化過程及現(xiàn)代紅壤化過程兩種對立統(tǒng)一的特征,指出紅壤元素遷移的順序���。此外���,系統(tǒng)研究了紅壤的水分���、養(yǎng)分循環(huán)、退化過程與有關(guān)物質(zhì)循環(huán)的相互作用規(guī)律���,開創(chuàng)了我國紅壤物質(zhì)循環(huán)綜合研究的新思路���。
長期以來,國內(nèi)外土壤學(xué)者對紅壤的成土條件���、基本屬性進行過大量研究���,但對紅壤現(xiàn)代成土過程的本質(zhì)、物質(zhì)遷移轉(zhuǎn)化規(guī)律���,特別是紅壤發(fā)育年齡等問題尚未能深入闡明���;同時過去對紅壤研究多采用野外與室內(nèi)的靜態(tài)方法,缺乏長期定位與動態(tài)的系統(tǒng)研究���,在論證成土過程與發(fā)育年齡上���,也缺乏定量依據(jù)���。
為了進一步闡明紅壤形成過程與發(fā)育年齡,趙其國在江西鷹潭中國科學(xué)院紅壤生態(tài)試驗站���,利用排水采集器等裝置���,通過定位觀測與計算機模擬���,在我國率先開展了紅壤水熱動態(tài)規(guī)律���、物質(zhì)遷移與平衡的定位觀察,并從動態(tài)與定量角度對其成土過程與發(fā)育年齡進行深入研究���,先后發(fā)表了論文百余篇���,出版專著4本,多次獲得國家及中國科學(xué)院的嘉獎���。中國科學(xué)院院士任美鍔���、李連捷���、吳征鎰指出:“中國紅壤及區(qū)劃專著是我國當(dāng)前熱帶、亞熱帶土壤研究的指導(dǎo)性專著���,具有國際先進水平���。”
此外,在趙其國的領(lǐng)導(dǎo)下���,中國科學(xué)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“土壤圈物質(zhì)循環(huán)開放研究實驗室”���,培養(yǎng)了一批青年科技骨干,從事土壤圈物質(zhì)循環(huán)的研究���。為了擴大研究工作的影響和推動世界范圍內(nèi)的合作研究���,趙其國還創(chuàng)辦了英文版的《土壤圈》雜志(Pedosphere ,1991年2月創(chuàng)刊)���,向國內(nèi)外發(fā)行���。
近年來���,趙其國又將目光瞄向了清潔生產(chǎn)和生態(tài)高值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等方向,不遺余力地在祖國大地上奔走���。過去他就有一個習(xí)慣���,不管在國內(nèi)還是國外,只要開學(xué)術(shù)會議���,回來必定寫一個會議綜述在《土壤》雜志上刊載,將聽到的���、看到的國際土壤學(xué)研究的最新進展介紹給大家���,讓未參加會議者也能迅速了解到學(xué)科發(fā)展的最新情況。
如今���,已進入耄耋之年的趙其國更加關(guān)注國內(nèi)外土壤學(xué)科的發(fā)展和變化���,他說:“我最近主要考慮土壤學(xué)這個學(xué)科發(fā)展當(dāng)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���,比方怎么在時間、空間上作一個發(fā)展路線的頂層設(shè)計���,從時間上提出土壤學(xué)發(fā)展的路線圖���,從2020年到2050年中國的土壤科學(xué)研究怎么進入到世界前沿的水平。”
永遠忠誠黨的事業(yè)
■趙其國
今年(2001年���,下同���,編者注)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建黨80周年。我是1959年入黨的���,到今年已有42年���,雖與黨的歷史相比,我入黨的時間并不算長���,但入黨后這幾十年的經(jīng)歷���,卻不斷激起我終生難忘的對黨的深情回憶���。
新中國剛誕生不久,正是由于共產(chǎn)黨的領(lǐng)導(dǎo)���,我才有機會進入大學(xué)���。在大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期間,我在政治思想上初步有所提高���,開始認識到���,作為一個大學(xué)生的責(zé)任是,應(yīng)該做到又紅又專���,為新中國的建設(shè)事業(yè)作出自己的貢獻。
大學(xué)畢業(yè)進入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后���,在黨的教育與培養(yǎng)下���,使我認識到���,這是我畢生經(jīng)歷的重要開端,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���,應(yīng)該按黨的要求���,“刻苦努力,謙虛謹慎���,奮發(fā)圖強”���。并應(yīng)用共產(chǎn)黨員的標(biāo)準(zhǔn)要求與鍛煉自己。為了爭取入黨���,我曾用自己學(xué)習(xí)與工作的實際行動���,接受了黨組織對我近5年的考驗,最后終于加入了黨���,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(chǎn)黨員���。從此���,我接受黨的教育與幫助就更加密切了。
長期艱苦的野外科學(xué)考察���,是我40多年科研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���。除了青藏高原外,我?guī)缀跖鼙榱巳珖鱾€角落���,記得每當(dāng)我在祖國南方熱帶雨林高山深谷中采集標(biāo)本���,風(fēng)餐露宿時,每當(dāng)我在祖國東北沼澤及北大荒考察���,迷失路途���,忍饑挨餓時,想起了黨���,想起了黨對我們共產(chǎn)黨員“艱苦奮斗,不畏艱辛���,努力攀登科學(xué)高峰”的教導(dǎo)���,不少困難均迎刃而解���。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分隊在東北大興安嶺沼澤進行科學(xué)考察,我們乘坐的拖拉機在黃昏時突然損壞���,大家只好背著標(biāo)本徒步行走���,想不到在黑夜中穿越沼澤時,有同志身體虛脫昏迷���,我們就相互攙扶向前���,但在前進時突然迷了路,大家心情都十分慌張���。就在這時我們想起了紅軍長征的情景���,想起黨的艱苦斗爭的歷程與教導(dǎo),我們大家不由自主地哼起了“紅軍不怕遠征難”的歌曲,相互鼓勵���,在黑暗中共走了10個小時���,終于在天明到達了宿營地。
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���,我也時常遇到不少困難與挫折���。例如,當(dāng)紅壤研究工作缺乏經(jīng)費與項目時���,當(dāng)土壤科學(xué)研究受到社會及國際影響曾一度出現(xiàn)低谷時���,當(dāng)基礎(chǔ)與應(yīng)用,學(xué)科與需求之間出現(xiàn)矛盾時���,常使我感到極為困惑���。但想到黨的“堅持不懈,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”的精神與教導(dǎo)���,使我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���。最后使我正確處理好了任務(wù)與學(xué)科的關(guān)系。堅持了土壤所正確的研究方向���。
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幾年的農(nóng)村下放生活中���,每當(dāng)我思想出現(xiàn)極度委曲與不滿時,每當(dāng)對整個形勢產(chǎn)生疑惑與不解時���,正是我堅信黨的事業(yè)必然的光輝前景���,才使我較平靜地度過了三年多的困難時刻,逐漸回復(fù)到了正常的工作與生活���。
由于受到黨的長期教育與培養(yǎng)���,使我有幸連續(xù)三次被選為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,參加了黨的第十三���、十四與十五次代表大會���。這是我畢生難忘的經(jīng)歷���。在這段時間里,我親眼目睹���,親身體會到我們黨的光輝與偉大���。深刻認識到,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���,在以鄧小平與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黨的兩代領(lǐng)導(dǎo)下���,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(shè)事業(yè)的突飛猛進的成就與光輝前景。作為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我始終感到十分自豪���。
記得十年前在東京召開的國際土壤學(xué)大會上���,當(dāng)我作為中國代表第一個向全會作學(xué)術(shù)報告后,不少來自港澳臺的同胞���,含著熱淚握著我的手說���,“感謝你代表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(chǎn)黨向世界顯示了我們的科學(xué)成就���。”對此,我內(nèi)心的激動是至今難以忘懷的���。此后,我在幾次國際受獎會上被授獎時���,我都覺得是代表中國人民接受榮譽的���,因為,這種榮譽應(yīng)首先歸功于黨對我的長期教育與培養(yǎng)���,如果沒有黨的長期教育與關(guān)懷���,也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一切。
我們黨已創(chuàng)建80周年了���,這80年來也經(jīng)歷了無數(shù)艱險與困難���,但我堅信���,在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(lǐng)導(dǎo)下,我們黨及祖國的建設(shè)事業(yè)���,一定會更加繁榮昌盛���,前途必將更加燦爛輝煌。
我今年已進入古稀之年���,在人生的旅途中���,所剩下的日子已不多了,但作為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���,我決心用自己僅有的余年���,永遠忠于黨的事業(yè),為土壤科學(xué)事業(yè)的創(chuàng)新與發(fā)展���,為土壤所的學(xué)科建設(shè)���,為青年人才的培養(yǎng)與壯大���,作出自己應(yīng)有的貢獻,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紀念建黨80周年���。(本文系作者為紀念中國共產(chǎn)黨誕辰80周年而作)
精彩語錄
趙其國:我在幾次國際會議上被授獎時���,我都覺得是代表中國人民接受榮譽的,因為���,這種榮譽應(yīng)首先歸功于黨對我的長期教育與培養(yǎng),如果沒有黨的長期教育與關(guān)懷���,也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一切���。
本文源自:《中國科學(xué)報》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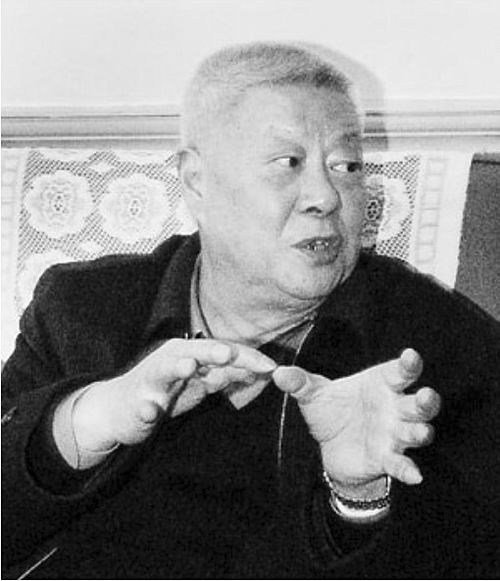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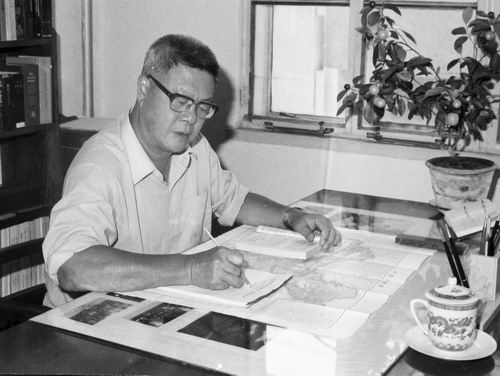



 蘇公網(wǎng)安備32059002004880號
蘇公網(wǎng)安備32059002004880號